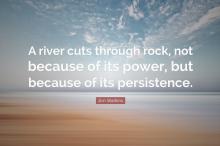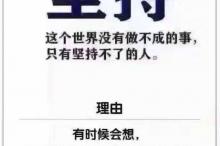知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朱大可著作《长生弈》

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
八年前朱大可虽然计划“将义无反顾地从汉语书写的前线撤离”,但在这些年里,朱大可在文化批评领域里面仍然不懈进行一种高难度的自我较量,善于勘探复杂的文化现象,建构自己独特的观察方式和理论视界,从而寻找到当代文化与历史传统之间的秘密而清晰的通道。 从文化批评向小说创作继续拓进,是朱大可另一个新的场域。最近,他出版了首部历史魔幻长篇小说《长生弈》,这是他近年来在文学形式上的新尝试,也是他以一个类型小说的外壳,装着纯文学的关于人类命运的终极探索。近日,朱大可前来深圳参加《长生弈》新书发布会,活动结束后,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。
原型是那种最具本质性的人性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《长生弈》可视为您对历史和神话领域的继续钻探,这也是您首部历史魔幻小说,为何您要以这种写作方式去继续响应它所提出的世界性难题?
朱大可:负责实现长生的应该是生命科学,消除死亡恐惧的是宗教,努力劝人放弃长生欲望的是哲学。跟这三种学科相比,小说其实是非常软弱的。但它的长处,在于能用故事营造长生的梦想,同时也可以摧毁这种梦想。在传达作者的世界观方面,小说比任何学科都更加自由。它是以上三种学科的总和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《搜神记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聊斋志异》主要写的是中国古代神祇灵异,探究历史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,而您也说这三部著作是您的写作范本?
朱大可:这三本书是中国文学的典范,也是我学习汉语叙事的教科书,它们不仅提供了故事原型,而且也帮助我理解古人的信念、欲望、生活场景及其方式。它们制造了一些由符号组成的孤岛,并诱惑我们前去旅行,跟那些古老的灵魂相遇,倾听他们的独白。要是没有这些古小说的存在,任何现代写作都是难以为继的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同样是以中国神话及历史为题材,但相较于鲁迅的“只取一点因由,随意点染”,您似乎更有意要表达您的中国文化观?如何理解您在讲这些中国故事的现代性?
朱大可: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当然是“新传奇”的代表。在民国年代,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,能够像它那样,展示出一种遗世独立的苍凉气质。但我考虑更多的,还不仅是小说的气质,而是它所拥有的原型。所谓原型,就是那种最具本质性的人性,能够表达超越时空、亘古不变的欲望。它既是最古老的,也是最现代的。这是神话原型的力量,它能够超越数千年的岁月,直接击中当代读者的灵魂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“长生”是贯穿小说的关键词,您通过各种人物演绎去呈现您对“长生”背后的文化根系的理解,这涉及探讨的还是生死观、宇宙观问题,今天您再提“长生”,是觉得我们的生死观、宇宙观出现问题了吗?
朱大可:“长生”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执念,它源于道家和道教的信念,并且在魏晋时期成为士大夫的时尚。经过近两千年的培育,现在成了国人欲望体系的核心成分。即便在上世纪某一时期,气功、养生和广场舞,仍然是世人孜孜不倦的生活主题,否则,我们就无法听到那些关于鸡血疗法、盐卤疗法和红茶菌疗法的传奇故事了。今天流行的干细胞疗法,以“高科技”的名义,重写了这种古老的欲望。《长生弈》没有打算否定这种古老的意志,而是要为长期受挫的欲望,找到一个可以放弃的理由。与其谋求没有质量的生命长度,不如让短暂的生命变得更有质量,而这才是更加正确的生命观念。
史料是钢筋,魔幻想象是水泥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您说过,写历史/魔幻长篇小说,是一种繁琐的事务,它不仅需要自由的想象力,还需要缜密的历史考据,那么在写作过程中,您是具体如何平衡魔幻和历史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元素?
朱大可:我们掌握的史料大多是支离破碎的,在史料之间,存在着巨大的缝隙。而魔幻想象是填补这种缝隙的最佳材料。你可以把史料看作钢筋,而把魔幻想象视为水泥,它们就这样被仔细地搭建起来,形成坚固的文本建筑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对于中国神话及历史,在时下往往更被网络作家所青睐,成为一种类型小说题材,广泛运用于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。相反,纯文学领域的作家则少有人问津。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?为何这种题材不入主流文坛的写作?
朱大可:这的确是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。我的看法是,大多数年轻作者缺乏生活经验,只能利用丰沛的想象力来改造小说的气质,而大龄作者想象力衰退,却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,所以会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写法。这是文学书写的一种隐秘规则,很少有人能摆脱这种规则的限定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在高科技迅猛发展、太空探索不断推进的今天,我们来谈论历史与神话,更增加几分开放性和神秘的意味。那么现代科技跟历史神话研究,彼此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呢?
朱大可:神话与科技,过去是彼此对立的两类元素,而现在则面临大融合的趋势。好莱坞近年推出的作品,如影片《神奇女侠》《神奇博士》和美剧《神盾局特工》,都是神话加科幻的混合类型,而且饱受观众的欢迎。所以,在高科技的语境下从事历史与神话的书写,应该不会有什么违和感,相反,它可以大幅度拓展我们当下的阅读经验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中国的神话与历史故事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都非常丰富,但就目前来看,跟现代人的生活似乎比较无甚关联,您认为随着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,神话会逐渐消失吗?它还能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源头吗?
朱大可:狭义的神话,是上古居民在宗教活动中形成的想象性文本,它们距离我们有些遥远,但广义的神话,则包括所有被“梦工厂”制造出来的当代文艺作品。这些现代神话已经占领了人类的书本、电视、电影和手机。没有这些被不断制造出来的新神话,人们又如何安放自己焦虑而惶惑的灵魂?